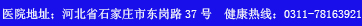无为往事丨泥汊大港滩情结
2022/6/4 来源:不详北京雀斑医院电话 http://pf.39.net/bdfyy/bdfzd/211211/10059087.html
泥汊大港滩情结
赵朝荣
几年前的一天,秋高气爽,晴空万里。我沐浴着夕阳余晖,漫步在村村通的水泥大道上,来到泥汊木马地村。我下意识地向右拐,沿着大港埂继续向南散步,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大港的大兜包湾处,眼前的景象把我迷住了。这里已经改造成一片良田。稻子已成熟,金灿灿的一片。这里人少空气新鲜,没有车辆。很安静而且开阔。从此以后我便常来此散步。
这一片港滩地是一名种田大户承包的。都是机械化操作。稻子收割完后,马上就种上了冬小麦。春天来这里,一眼看不到边的,都是郁郁葱葱的遍地绿色,到处充满生机。去年承包的老板又改种植为养殖。将这一区域重新规划。四周新造了大埂,中间形成一块块的鱼塘,整齐划一。其间放养蟹鳖鱼虾等,放眼望去又是一派新的景象。看到眼前的一切,使我自然地想起五十年前的景象。
大港实名叫金斗港,是金斗、皂河、三溪几个村的重要水系之一。它由三段组成,南北走向,流向夹河。北端从木马地的荷包塘开始,这里水深塘大,向南连接大港。继续向南走不到米,靠东边港埂一侧,便出现很大的一个兜包湾,湾中间是浅滩,湾四周稍微深一点,两侧是主水道,更深些。这一地带面积大,很开阔。再向南走一点,大港就明显窄多了,有明显人工开挖的痕迹。所以说金斗港是人工和天然合成的。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其实就是一片沼泽地。港滩周围没有像样的大埂,而是造港埂留下的环滩沟。除深的水域外,到处都长满了芦苇、蒲草之类。这片看似荒凉的水域,却是我们65岁以上的老人们赖以生存的一个重要地方,这片水域对我们有恩,故作此文以示后人。
在我的人生中见过最大的水灾是年江埂决堤,家乡一片汪洋,我们不得不搬到离故土几十里之外的山区栖身。为了活命,灾民们有的到江南各县逃荒,有的做些小本生意,或者做些手艺活糊口。我的父亲年轻时会织网捕鱼,遇上荒年,爸爸常和大伯俩外出捕鱼,大伯是打旋网的高手,每天到晚归来,总能捕到许多鱼。除供家人食用外,多余的就卖钱。第二年水退了我们又重返老家。后来家乡虽说没有破江堤,但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饿死许多人。
再往后分责任田,却是好景不长,又过上生产队大集体的生活。当时水利条件差,水灾不断,农民日子很苦,缺粮缺柴,吃不饱,穿不暖。我因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也中断了学业,回家务农。父亲买了网片,凭借他的装网技术,改装了一个虾拖子网,从此我们父子俩经常在金斗港里拉鱼虾,从清晨一直拉到天黑才回家。
拉鱼虾很辛苦,父亲划船,我在船舱里起网下网。在划船拖网期间,我就捡拣前网拉上来的鱼虾,把剩下的杂物等抛出船外,再起第二网。我开始干这活很不习惯.划船拉虾子,船桨吃水很深,用力猛划,船猛向前一跃,虾拖子网连在船舷上,在船后面水底拖着,阻力很大,便又将船往回一拉,一桨接一桨地划,船便进多退少地慢步一搡一搡地向前行。闹的人很不好受。不仅站立不稳,而且心里作翻想呕吐,头昏难当,晕船晕的厉害。船行一段距离把网起上来,倒下网中物,再把网沉入水中继续拉,没办法仍然坚持着。时间一长,这种晕船症状也就逐渐好转了。现在我已入古稀之年,女儿陪我去三亚旅游时,在南海坐游艇,风浪那么大,我一点也不晕船了。
往年拉鱼虾每天也拉不了多少,而且鱼虾价格也低。为了生存不能怕辛苦,每天早出晚归,中午用从家里带来的保温瓶装的稀饭打点尖。有一天收获特别大,我们有一网可能是拉到虾窝子里去了,船未行到位,我们发现虾拖子网漂浮出水面,鼓成一个大包,拉上来一看,全是大小差不多的虾子,很纯,没有小鱼和杂物,估计是虾王在召集大家开会,被我们一网打尽。那天我们运气好,拉了十几斤虾子、小鱼,还有五条大鱼,最大的有四斤多重,真是出了奇迹,我们高兴极了。
为什么虾拖子也能捕到大鱼呢?是因为父亲自己会装网,他装的网不仅网兜深,而且上方还有回兜,进网的鱼即使想逃跑,却被回兜拦住了,让它晕头转向,不知往哪逃脱,就被拉出了水。我爸用网片改装的网比买回来的现成的网灵验得多。在这一带捕鱼虾的不只是我们父子俩,还有很多人以各种古老的方式在捕鱼。
推网,是一个三角形的网,其中一角为网兜,连接另外两角的扁木条或短竹等叫做网刀口,再用一根长竹杆和网刀口正中固定起来,便是最简单的捕鱼工具了。主要在靠埂边的浅沟里推点小鱼虾,使用很灵活,一网接一网的推,把推到的小鱼虾捡起来放入挂在腰间的小篓子里。
虎网,主要是在浅滩上捕些小鱼。它的构造也很简单,用两根弓形竹子交叉地把一块网片的四个角连起来,网底是长方形,上面三方有网蒙着,一方空着为进鱼口。把网安放好,捕鱼者在空口处的前方水面走动泼水,让小鱼惊慌乱窜,捕鱼人往网口处边走边泼水,适时快速起网,被赶进网里的小鱼就跑不掉了。
木马地人们,个个会捕鱼,他们主要以捕鱼为生。荷包塘和大港滩两边的深水区是他们的捕鱼场所。他们每家都有腰子盆,在那个困难的年代,腰子盆对他们来说用途太大了,具有多功能性。不仅是水上交通和捕鱼的必备工具,而且晚上可以当门用,吃饭时把盆翻过来,盆底朝上当餐桌用。他们划盆的技术特别高,捕鱼时在水域两边下网,主要是丝网,网下好后,便在两网之间的水面上用手桨边划水边敲盆,并且弓着身上在盆上摇晃。像玩杂技晃板打蛋似的,人不会翻盆落水。有时他们不用任何划盆工具,只是空身人站在盆中颠簸,腰子盆自动会前进,掌握方向也很自如,这是靠脚下功夫。现在的人们看到这场面,会为他们捏一把汗的。而当时人们是司空见惯,无所谓的。他们这样在水上折腾,使鱼惊慌乱窜,撞到网上就跑不掉了。除此之外还有放卡子和钓子捕鱼的。
不仅是我们当地人在此捕鱼,也有下湖佬(专业渔民)他们有时不在河里捕鱼,而把小渔船拖到内圩来捕鱼,像在凑热闹。他们往往是夫妻俩在船上,妻子划桨,丈夫在船头下夹网和丝网等。然后用水雷在船前方和两侧用力猛捣,造成局部水声很大,让鱼受惊。水雷是像厚实的黑铁碗一样的物品。碗口朝下,上面按上一根竹竿,渔民拿着竹竿在水里乱捣,泛起大的水花,叫捣水雷。
夹网形状像很大的河蚌,长度约1.5米。河蚌网背上的固定支架上装两根交叉的竹杆,交叉点在竹杆的中下部,用灵活的轴固定着。下网时渔夫单膝跪在船头,把竹杆上端拉开,网便张开了,再用力按到水底下,碰巧能罩住伏在泥里不动的鱼,然后贴紧水底合拢竹杆,网口也就关闭了,再把双竹杆一把接一把的往上提出水面,网里面是否有鱼就一目了然了。
冬天还有徒手捕鱼的,这些人叫摸鱼佬。冬天有些鱼钻在泥坑里或水下埂洞里不动。摸鱼人往往只穿短裤,上身穿着破旧棉袄,右胳膊和肩膀都露在外面,随时探到冰冷刺骨的水里摸鱼,碰巧也能摸到。水里的鱼碰到他们的手就跑不掉。这一行很辛苦,那个年代没有像现在渔民捕鱼时穿的连胶鞋在一起的胶鱼裤,那时连深筒胶鞋都买不到。冬天摸鱼只能光着腿脚下水。天暖和是摸不到鱼的,因鱼活跃不潜伏淤泥和埂洞中。因此摸鱼佬们到老年时大部分人都患有筋骨疼病。
为什么那么多人捕鱼而鱼虾仍然不绝,主要是没有电捕,现在用电瓶打鱼,大鱼被打死打晕,小鱼全死;没有药物捕;不用炸药炸鱼。这几种捕鱼方式会让鱼类断子绝孙。当时水路通畅,沟塘河港相通,埂上到处是缺口,鱼类能自由畅游,而且水质好,不使用化肥农药,无水源污染;每年旱情严重时,要从长江放潮,每道闸、坝、斗门等都没有各式各样的网阻拦,江鱼和大量鱼籽随水放入了内圩,不用人工放养,鱼苗数的密集度就很大,成鱼数量便多了。品种也多,如刀鱼、鳗鱼、刺姑鱼、刀鳅等,这些鱼种在圩区现在已看不到了。
昔日除在大港渔场外,其他沟塘鱼虾也很多。在夏天妇女、姑娘们用小棉布做成虾筝扳虾子,晚上在塘边纳凉带扳虾子,扳到的都是亮晶晶半透明的大虾。在深秋季节,有些人在朦胧的月光下或漆黑的夜晚,她们点着小风灯用渔网张河蟹,她们不畏寒意袭人,全神贯注地守候在水塘边,经常守到半夜,张到的河蟹又大又肥。肉质鲜嫩丰满,七八两一只的也不稀奇。现在再出高价市场上也买不到那样的蟹虾了。这可能就是老一辈对昔日大港滩的思念而产生浓厚的怀旧情感的原因吧!
作者简介:赵朝荣,无为泥汊人,年9月生,三溪中学退休教师,从事语文、英语教学40年。爱好文学、书法和美术,喜欢写些文章和诗歌,曾在《合肥晩报》上连载过文章。热心公益事业,曾受无为市和芜湖市关工委表彰。
来源:原野牧歌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