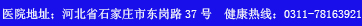宜丰儒溪十桥
2024/12/12 来源:不详儒溪是蜿蜒在古阳寨之下店上村的一条小溪。儒溪名之由来,已不得而知,古人对河流的命名与现在不同,一条河流因经过的地方不同,常常会有不同的名称,因此考证时颇为复杂。如耶溪,它的上游称藤江,下游又称凌江,而中间这段却称盐溪。按古《新昌县志》记载,耶溪仅是指流经宜丰县城这段,并非是整条河流的统称。而今在宜丰县行政地图上,又在耶溪的名称上增加一个“河”字,称作耶溪河。将“溪”和“河”两字同时为一条河流名称,竟没人发觉有任何的违和感。古人对文字非常考究,《新昌县志》中没有发现“某溪河”的水名。
图为儒溪风光
儒溪处在藤江的上游,于袁家洲汇入洑溪,当地人一直称其为大港。而本文所述的儒溪不是指这条河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儒溪之名早已退出历史,改称石莲河。公元年,以店上村境内的莲花山名成立莲花大队,以古石桥名成立石桥大队,将流经两地的大港称为石莲河。在此之前,经店上村的水流除了自石桥方向来的大港外,还有一条自古阳寨山区来的溪流,当地人称细港。店上村也曾称儒溪,可在清同治十二年的《瑞州府志》上得到证实。故可推测,古代文人雅士把流经店上村的水域都称为儒溪,而在民间则分称大港和细港。大港之名被石莲河取代,而细港仍被称为儒溪。本文重点介绍的就是横跨在这条细港之上的十座古桥梁,故称“儒溪十桥”。
图为《瑞州府志》中将现店上村位置标注为儒溪
儒溪的源头在古阳寨山区,涓涓溪流自东向西注入洑溪,总长度约为三公里,与一条南北向的古商道形成十字交错的形势。自古以来,人们沿儒溪建立多个村落,为出行方便,架设桥梁之多,乃是宜丰县境内罕见的现象。这十座桥梁的名称分别是张家桥、奥米桥、美市桥、儒溪桥、上码头桥、庙前桥、南桥、下山桥、邓家桥、万福桥等。其中除张家桥被拆毁,其它九桥仍横跨在溪流之上,有的仍在使用,有的则被遗弃在田野和山林之中。
图为沿儒溪而修石板路
笔者儿时曾在潭山老街生活十数年,经常自潭山老街的万寿宫溯细港而上,抓小魚小虾,或沿细港两岸的护堤采摘野花桑叶,故对临近老街的张家桥、奥米桥、美市桥等较为熟悉,而靠近古阳寨大山的南桥、下山桥、邓家桥、万福桥等则从未见过。
图为儒溪周边风光
一年前,常与店上村委陈仕才谈论儒溪十桥的现状和传闻,遂勾起童年的回忆和对未知之桥的向往,便相约今年开春同去考察。但因上半年雨水不断,接着又是三个月的高温暴晒,故拖到十月中旬才成行。
从潭山集镇大街的儒溪与洑溪汇合处出发,首先跃入眼帘的便是张家桥的遗址,它处在大街楼宇的夹缝之中,而四十余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田野。这座桥由胡家垄张氏族人所建,是潭山老街通往逍遥的必经之路。按清乾隆壬子《新昌县志》记载,全县有二十一大墟市,胡家垄市(又称袁家洲市)便是其中之一。查清康熙年间的《新昌县志》没有胡家垄市的记载,故可推断兴市时间较晚,约在清乾隆年间。胡家垄处在大港与洑溪的汇合处,明清时期也建有一座石桥,称步云桥(又称袁家洲桥),由当时大学士邹维瑚始建。
图为儒溪周边风光
从张家桥遗址处沿溪堤向上,溪道大部分淤塞,只剩下涓涓细流,早已没有了先前溪流喧哗和清澈见魚的风光。记得小时候,岸堤上的芦苇和灌木非常少,可在两边溪堤的小路上一直行走,而今溪堤荆棘满布,无容身之处。想当年受生活条件限制,村落周边的芦苇灌木经常被砍去用于炊事,而当液化气进入万家后,没有人会再去做这些“无谓”的劳作。
辗转来到奥米桥,它隐身在芦苇灌木丛中,仅露出部分桥面,拔开灌丛才能窥视其部分。奥米桥是一墩两瓮结构的石拱桥。桥面上排列着整齐的石板,表面仍光滑如旧。记得以前桥的两端都有石阶,但现在荡然无存。桥身刻有“奥米桥,大明正统已未年,天宝三十三都义门陈氏合族建”铭文。该桥建于明正统四年(公元年),距今有年的历史。
图为露出的奥米桥桥面
“奥米”之名出自现店上村曾经是古代著名的大米交易市场,但“奥”字作何解读?则众说不一。在清康熙乙巳《新昌县志》中,仅记载一处带有“奥米”的地名,即“奥米后坊”,之后在清乾隆壬子《新昌县志》中又出现“店上”和“宅前”两处地名。将地名编入县志,是古代县署用于地方保甲和赋役的依据,把“奥米后坊”、“店上”和“宅前”并列,说明不是同一地方。目前,三处地名仍在使用,但“奥米后坊”则去掉了“奥米”两字,称为后坊。在《盐乘》氏族一考中,目前居住在店上村的陈氏称为“后坊陈氏”,说明后坊乃是陈氏的发祥之地。因此,“奥米”与后坊存在必然的关联。
“奥”在《说文解字》中有:“宛也。室之西南隅”。《康熙字典》中与“墺”通,有:“室西南隅,人所安息也”又有:“五祀之祭”和“积聚”。同时与“澳”和“隩”通,指河岸弯曲的地方。以“奥”字来解读后坊:一是儒溪以“弓”形绕过,二是在后坊西南隅的下水口处刚好有座福主庙,旁又建有一桥。从这些资料来分析,后坊乃是奥米中的“奥”字的原始出处。后坊是陈氏的发祥之地,随着人口发展,一些具有营商天赋的陈氏族人首先迁到古商道上,开辟大米交易市场,称为米市。陈氏族人完全按照后坊的风水局来规划市场,故称“奥”,由此便有了在市场入口不远处建一庙,称奥米庙,在市场西南下水口处建一桥,称奥米桥。按清康熙乙巳《新昌县志》记载,奥米市在元代就形成有影响力的墟市,属当时全县十一大墟市之一。
当地传说奥米桥原是一座木桥。明朝期间,奥米曾有一陈氏女子嫁到洑溪吴家,该女子思念衰老的母亲,经常回奥米娘家探望,木桥常常遭洪水冲毁而不能相见。族人为该女子的行为所感动,便倡议建一石桥,以遂女子之愿。经仔细分析,该传说存在一个明显的漏洞,因为往前再走一百米便是美市桥,何来木桥损毁阻隔之说呢?实际上这里是奥米市的下水口,在此处建桥是出于风水布局的考量。可能奥米桥原是一座木桥,且修且毁,故在明代,陈氏族人痛下决心,花费巨资建造一座高大的双拱桥。后人为弘扬孝义,又给此桥赋予了具有教育意义的传说。
图为被杂丛遮挡的奥米桥
从奥米桥再往上一百米便是美市桥。美市与米市谐音,桥名即说明了市场的经营项目,又表达了对市场前景的美好愿望,可谓一语双关。美市桥处在古商主道上,通过此桥便可到陈氏“真良家”门楼,而门楼之内便是店铺林立的米市,吃、住、游、购一应俱全,大大方便了来自各方的商队。
图为美市桥现状
美市桥由一墩十梁双跨构成,桥面宽敞,可容两辆独轮车并行,相比奥米桥而言则又显得矮小简单,但经济适用。桥身仅有“美市桥”铭文,没有镌刻建桥时间。从其所处位置的重要性来分析,应是奥米兴市不久建造,建造时间比奥米桥更早。
图为美市桥周围环境
不经美市桥,沿溪往右行走一百米左右便是儒溪桥。陈氏十世淑惠公携家从儒溪西岸分居东岸。在风水先生的指点下,选择在一樟树下架木桥,方便与西岸的族人来往。明永乐年间,淑惠公支下人财兴旺,其后裔聚居处先以细港之名,称港下,后又倡儒学之风,称儒溪,这是细港被称为儒溪的缘由。由于经常受山洪困扰,族人用石垱将村落围住,又将原木桥改建成一墩六梁双跨的石桥,取名为儒溪桥。随着时代的发展,儒溪桥无法满足机动车辆通行,为保护该桥,在上方不远处新建一座钢混水泥桥代替。
图为儒溪桥现状
图为下港围垱豁口门楼构件
由儒溪桥继续往前便是一片广袤的田野,一座一墩四梁双跨的石桥隐身在其中,称上码头桥。顾名思义,码头一般是指水运或摆渡的停靠之处,但儒溪狭窄水浅,无法船行,似乎与码头牛马不相及。原来此处溪流开始平缓且较上游水深,从山里砍伐而来竹木一根根顺流到处,再编织成小筏,继续往下游运送,故此地称上码头。上码头桥的桥身较窄,每次仅能容一人通行,是连接古阳寨、奥米和潭山老街三地的便道,同时两端均是稻田,又便于两岸日常农耕来往。从上码头桥的风化程度观察,年代非常久远,石块呈青绿色。尽管上码头桥结构普通,但也有其独特之处,一是桥墩位置不是处在桥的正中,而是偏向一边,这样形成一宽一窄的水道。二是桥墩的分水尖不是正对着水流,而稍微地侧向较窄水道一边,这样的设计显然是出于安全放筏的考虑。
图为上码头桥现状
上码头桥的上游便是庙前桥。庙前桥处在田背里的西南隅,因距桥不远处的大樟树下有一座用石块雕琢而成社令祠,也称土地庙,桥名由此而来。早在北宋末年,陈氏先祖爽公迁居于此,因处在山坳与水田的结合处,故地名为田背里。
图为庙前桥现状
图为庙前桥不远处的社令祠
田背里位于儒溪中游,溪流从村落北面到东面,又拐弯到村落的南面而去,故村落每年都要面对山洪爆发的威胁。来到田背里,会被陈氏族人为战胜水患的创举感到惊叹!在村落四围用条石砌成两米高的围垱,仅在村落的西面留出一豁口出入,并在豁口处挖掘数口池塘蓄水。垱上遍植樟、株、竹等根系发达的植物,起到加固围垱的作用。世人都知道洑溪村有“古树长廊”,却不知田背里的围垱比“古树长廊”的规模更大,保存更完整,垱上至今还保留着不少高大的古树。田背里也是一座透过风水布局形成的村落,如在围垱的西南处建一社令祠和在下水口处建一桥,又在豁口处挖池塘和建门楼等等,处处体现出陈氏族人对美好家园的渴望和追求,也是研究赣派古村落形成的重要资料。
图为田背里护村围垱
图为田背里围垱豁口门楼
庙前桥因有铭文:“明正德壬申,田背族人捐资兴建”故可知该桥建于公元年,距今有年历史。该桥为一墩六梁双跨结构,是古阳寨通往潭山老街的主要通道,山中的竹木和火纸源源不断地经过该桥销往外地。
图为田背里风光
图为田背里风光
在田背里北端的外围还有一座单拱桥。儒溪上仅有两座拱桥,除了奥米桥外,就是这座,因处在中宅的南面,故称南桥。南桥经今年春维修和周边环境整理之后,完整地露出其矫健的身姿。桥瓮用整齐划一的石块垒砌而成,建桥工艺精湛,远远望去显得非常牢固厚实。桥两端均是数级石阶,但没有设置车载匝道,可见此桥用于行人,而非用于车载。站在桥上,发现桥的北面是一片空旷田地,内心中总会油然生出建此规格的桥梁是何目的?据说空旷的田地原是一个村落,叫中宅,自清嘉庆年间起,居民陆续外迁,房屋逐渐荒废倒塌,如今已看不出任何的痕迹。桥洞中刻有:“天宝三十三都陈石渊妻邹氏,男通道、胡氏,达道、胡氏,远道、刘氏,孙进隆、进荣、进魁、进超、进趟、进笏、进道。正德辛未年八月日修,匠蒋玉辂造”铭文,原来南桥是由邹氏带领三子三媳和七个孙儿于明正德十年(公元年)八月建造完成,距今有年的历史。邹氏是陈石渊(又称陈硕渊)妻子,关于此桥当地有个感人故事。陈石渊夫妇居住在中宅,平时出行均要涉水,夫妇俩商议建桥,开始通过日常辛勤劳作来积攒建桥的费用。不知攒了多久,于明正德九年(公元1年)八月正式开工,可是两个月后,六十九岁的陈石渊不幸病逝。邹氏为完成陈石渊的心愿,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带领儿孙们筹银建桥,终于在次年八月桥梁竣工。邹氏因此受到族人称赞,以八十五岁的高寿去世,故南桥又称为寡妇桥。
图为南桥现状
南桥的建造规格可与由族众共建的奥米桥媲美,故事中关于陈石渊夫妻依靠日常耕作来攒费建桥之举则有些让人不信。试想,如果陈石渊夫妻真是解决涉水过溪的问题,完全没必要建一座费时、费银、又费工的石拱桥,不如建座简易的石板桥用于通行更实惠,而建如此高规格的桥梁却显得有些炫耀,反而更能说明陈石渊家境殷实,并非一般普通农户。在宜丰,笔者所知的寡妇桥就有三座,除了儒溪这座南桥,还有中兴村的下石桥和洞上的逢渠桥。这些所谓的“寡妇桥”,都是古代倡导妇女“贞节”之风衍生而来。
图为南桥远景
从南桥出发继续往古阳寨方向的石板路前行,便来到下山桥。本文开篇就提到下山桥,它是后坊进出的唯一通道。桥端直面一石壁,不远处有座庙,它们都是后坊风水布局的组成部分。下山桥是一墩六梁双跨结构,桥身刻有:“阿弥陀佛”和“田背蒋氏立”字样,带有明显地镇煞作用。桥墩似乎是用未经规整的石块随意堆砌而成,有摇摇欲塌之感。但数百年来,经历了无数次的山洪而屹立不倒,其背后肯定暗藏着玄机。
图为下山桥现状
再往上游便是邓家桥,因是邓家屋场出入通道而名。邓家桥属单跨石板桥,今改造成公路桥,看不出任何的原始痕迹。明末期间,邓氏由芳溪禾埠迁此。如今邓氏早已迁走,由其他姓氏在此居住,空留一桥名。
图为邓家桥现状
儒溪的最后一座桥便是万福桥,过桥再往前走就进入古阳寨山林。明洪武年间,庙下刘氏购下这片山林,在此开辟纸棚和庄园,因位于东坑之南,故名下东庄。而万福桥则在下东庄的下水口,为一墩六梁双跨结构。不久前,在附近的田边发现一块当年建桥时的功德碑,仅能辩认出“民国十年吉立”字样,故可证实该桥建于公元年,属儒溪十桥中,建造时间最晚的桥。关于万福桥名的来历也有一个故事,据传有一位拾荒老人来到下东庄,寄居在原木桥大樟树下的土地庙里,靠庙里一些供品以及过往行人和村民施舍为生,老人逢人便作揖念道:“万福!万福!万福!”。人们不知他姓氏名谁,便称呼他为万福。万福老人经常帮助村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义务劳动,慢慢地被村民接纳并特意空出一间茅屋,让他从庙里搬来居住。当万福老人得知村民准备将木桥改建成石桥时,不仅将平日乞讨而来的积蓄全部捐出,而且主动回到桥头土地庙居住,义务为村民看护工地。然而,当石桥准备于次日竣工时,万福老人当天白天无恙,晚上就去世在庙里。村民商议决定将石桥名为万福桥,并把老人的贴身遗物压在桥墩上的石板之下,让他的神灵永远看护此桥。
图为万福桥现状
儒溪十桥的建造时间从元代到民国跨越数百年,几乎每座桥都有一个传说。儒溪上的桥梁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在桥端迎水面种植一棵樟树,宛如站立在桥头的护桥神,即可护桥堤,又体现出当地独特的风水现象。
图为儒溪周边风光
儒溪不仅有桥,沿溪两边均筑起高高的堤岸,种植成排的树木,用于保护农田,故周边风光秀丽。想当年,竹木筏在桥下穿行,居民在溪边洗刷,好一派田园村落景象。儒溪不仅有桥,还有沿溪的石板路,这条路不知过往了多少人?发生了多少故事?人文底蕴深厚。儒溪不仅有桥,还有两处引水陂,是古人营造的灌溉工程,让大山中清澈的溪水滋润了四周广袤的农田,养育了世世代代在此生息的人们。
图为儒溪周边风光
图为儒溪周边风光
儒溪又是店上村一处绝佳的区域人文资源,不仅可以看到数百年来属于赣派古桥的演变,而且还可透过古桥,来发掘沿溪村落不为人知的历史。由于分布在野外,庆幸古桥躲避了现代建筑的摧毁,能让我们的后辈还能看到这些历史遗存,领略古村落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儒溪水道和护堤也要进行清理去淤,让它恢复往日的风貌,使其得于完整地呈现出来,为奔波在城市的人们提供一个踏古休闲的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