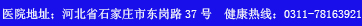航路,季风与洋流
2022/7/28 来源:不详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科学大讲堂 https://m-mip.39.net/czk/mipso_7637330.html
唐咸通三年(指日本贞观四年)玄月三日(年9月30日),日本和尚亲王等僧俗60人一行乘坐明州帆海家张支信亲身督造并掌舵的海船,从值嘉岛(平户岛及五岛列岛的旧名)向大唐进发。
玄月三日,从东朔风飞帆,其疾如矢,四日三夜驰渡之间。此月六日未时,顺风忽止,逆浪打舻,即收帆投沈石,而沈石不着海底,仍(乃)更续储料纲下之,纲长五十余丈,才及水底。此时波浪甚高如山,终夜不休,舶上之人皆惶失度,异口同音祈愿佛神,但见亲王神态不动。晓旦之间,民风微扇,乃观日晖,是如顺风,乍嘉行矴,挑帆随风而走。七日午尅(刻),遥见云山;未尅(刻),着大唐明州之杨扇山;申尅(刻),到彼山石丹奥泊,即落帆下矴。[1]
对于“杨扇山”到底在宁波的哪里,宁波场合文史行家杨古城和曹厚德老师曾觉得存在着北仑的杨公山、算山(合称杨扇山,距蛟门不远)或北仑的羊所山两种或者[2]。而林士民老师则觉得,“遵循舟山到宁波这一带的当然海流的流向与季风的风向所孕育的航路”也许估计,“云山理应是舟山群岛本岛,过二小时应是(金塘山)杨扇山,……再过二小时可达阿育王山下的岙口一带(即指文中的石丹奥。水银注)”,即今“璎珞河边和古阿育王溪东一带”[3]。
我觉得,杨扇山在穿山半岛北缘和杨扇山即金塘山(或其一部)的估计都难以创立,道理正在于这一估计实践上把宁波或镇海去日本或朝鲜的航路创设在超出金塘岛直接向北出洋的了解上。
往时在提到华夏到日本朝鲜的北路之北线南线、南路之北线南线(见图01)时,不过费解地说“从明州、定海(今镇海)登程”这样[4]。
图01
但船出甬江口(望海镇或定海县)后,到底是从舟山群岛的西边北上(下称西道),仍旧绕东边北上(下称东道),则语焉不详。大概是基于咱们二三十年前乘上海汽船的阅历,觉得从舟山群岛的西边北上之航路(见图02),是显而易见的吧。
图02
倘若以这类阅历(西道)做为前提,则将杨扇山认做是杨公山与算山的合称,还也许注释,——由于杨扇山做为东道上的对景,是长久从西道跑中日航路的张支信所不熟练的,于是他要再化一个时刻(两小时)从杨扇山向东驶到石丹奥(算山四周);但基于一样的阅历(西道),把杨扇山认做是金塘山,就注释不通了,——莫非“老司机”张支信到了金塘山后竟然认不得进甬江口的水路了?非要再化一个时刻折向东南边,驶向离明州城越来越远的育王山?
一、东道:高速海道的联结线
乘坐沪甬班轮,是咱们尚未忘记的生计体会,我曾经经过此而想当然地觉得,宁波到天津、朝鲜、日本的航路理当是出镇海口穿过金塘岛,岱山、衢山、嵊泗列岛后向东北。本文将此称之为西道。
郑和下西洋时,船队从浏家港登程,在浙东海疆的航路是过金塘岛以东的西后门(今名西堠门),斜插绕崎头角,过双屿门,自牛鼻山川道南下(见图03)[5]。看来郑和航路与西道有重合。遵照来回同路的估计,宛如宁波到日本朝鲜,也应走西道,先到长江口以东后,渡海过洋才是。
图03
其它,目前遗留住来的华夏保守帆海图,大多以连结的对景图组成,也让古人孕育了华夏人只长于沿海飞舞的错觉。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事件总管巴罗(SirJohnBarrow,-)因而而下论断道:“华夏人既不长于造船术,也一样不长于帆海术。他们没有海上船只场所的盘算法”[6],咱们以前尽管一万个不屈气,却宛如也无力辩驳。
沿海飞舞与远洋飞舞最直接的差别即是前者能看到陆上对景,可据以傍岸船行,不致迷途;此后者四顾茫然,不知身在哪里,倘若然的“没有海上船只场所的盘算法”,则北上高丽、东渡日本的远洋飞舞,即是破釜沉舟的赌钱。照这类说法,唐宋时代的海军们欲东渡日本,该尽或者地多走沿海(西道),而后在距日本近来的航路端点(如长江口)上,撒手一搏才是。
但实践上有不少史例讲明,宁波去日本朝鲜的航路,多出镇海口东绕舟山本岛(东道),从莲花洋出海切入远洋航路。
不愿去观音。先是,大中十三年()日本国僧惠谔诣五台山还礼,至中台精舍见观音貌像端雅,喜生颜色,乃就乞请愿迎归其国寺,众从之。谔即肩舁至此以之登舟,而像重弗成举,率偕行贾客极力舁之,乃克胜。及过昌国之梅岑山,涛怒风飞,舟人惧甚。谔夜梦一胡僧,谓之曰:汝但安吾此山必令便风相送。谔泣而告众以梦,咸诧异。相与诛茆缚室,敬置其像而去,因呼为不愿去观音。后来开元僧道载复梦观音欲归此寺,乃刱建殿宇,迎而奉之。邦人祷告辄应,亦号瑞应观音。[7]
“昌国之梅岑山”,即今普陀山,其旁的“莲花洋”,即是因这个“不愿去观音”的传闻而得名。这明了地讲明,唐朝宁波渡日的航路,走的是东道,即是东绕舟山本岛从沈家门而出洋的。
其它,舟山普陀的地名,有“新罗礁”、“高丽道头”,据考据,它们正处在普陀山西南面的海疆和陆上[8]。这最少阐明,在野鲜半岛曾被指称为“新罗”、“高丽”的年头,东道便曾经存在。
北宋宣和年间去高丽的使节神舟船队,也是走东道,过沈家门、梅岑山(普陀岛)后北上;回程时曾遇风暴,“使舟与他舟皆遇险不一”,大概因而而提早切入了沿海航路,乃由姑苏洋(疑为长江口),夜泊栗港(烈港),过蛟门,望招宝山而到定海县[9]。
到了明清之际,《指南针法》中的“宁波从前本针”、“回宁波针”,出入均经“普陀”[10],阐明东绕舟山本岛的东道,已被华夏海军们认做是最为牢固的航路。
最使人惊讶的,是明朝吴朴的《渡海方程》(),在这部被觉得是“华夏第一册刻印的水路簿”[11]中的“太仓使从前本针路”一节,是这么描画航路的:
太仓口岸开船,用单乙针,一更船,平。吴淞江用单乙针及乙卯针,一更,平。宝山到南汇嘴,用乙辰针出口岸。汲水六七丈,沙泥地是正轨。三鼓,见茶山。从此用坤申及丁未针,行三鼓,船直至巨细七山,滩山在东北边。滩山下水深七八托。用单丁针及丁午针,三鼓船,至霍山。霍山用单午针,至西后门。西后门用巽巳针,三鼓船,至茅山。茅山用辰巳针取庙州门,船从门下行过,取升罗屿。升罗屿用丁未针,经崎头山,出双屿港。双屿港用丙丁针,三鼓船,至孝敬洋及乱礁洋。乱礁洋水深八九托,取九山以行。九山用单卯针,二十七更过洋,至日本口岸。
又有从乌和尚开洋,七日即至日本。
若陈钱山至日本,用艮针。[12]
以上,“庙州门”指穿山半岛东端与洋小猫岛之间的航道[13],“升罗屿”即今升罗圆山屿,孝敬洋指象山口岸东边的洋面,乱礁洋为涂茨镇以东的洋面,而“九山”,即是韭山列岛。据第一段所述,可知从太仓至九山这段航路,险些与郑和下西洋的开端航路相同(参拜图03),差别在于到了九山后,郑和接续南下,而东渡日本则在九山(韭山列岛)处“用单卯针”(即正东向)折向东边,二十七更(天天一日夜为十更)三天不到,便可至日本口岸!看来,纵使往时(唐)曾有过太仓直航日本的航路(参拜图01),反而到了明朝时,竟然乐意绕这么大的弯(先南下后东北),转从韭山列岛北上日本,所何故来?
上引文第二段的“乌和尚”,在今舟山东南朱家尖四周[14]。显然,这说的,正是东道。
着末一段的“陈钱山”,即嵊山,今嵊泗县最东面的大岛。“用艮针”的道理是说从日本在嵊山东偏北15°的方位。
总之,明朝太仓从前本有三条航路,此中两条是太仓绕道舟山以东的乌和尚及南偏西处的韭山列岛,这生怕是把这两处认做是渡日的跳板了。
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旗舰“狮子号”暂泊于牛鼻山和布老门岛(今名东屿山和西屿山)之间,等来了定海总兵为船队找寻了两名去北洋天津的领航员后,从青龙港(即今梅山岛与佛渡岛之间的航道)北上。那末,出了青龙港后,马戛尔尼船队到底是往哪边出国的?是绕过崎头角过蛟门穿金塘而上,仍旧折向东过沈家门、普陀岛向北?从使团成员后来的著作中,宛如未见有详细论述,但从A/C两图来看,船队走的是东道(见图04)。而这条东道,当然是两位华夏领航员指的航路。
图04
从海图上看,出甬江口后的西道与东道之差别,正在于后者更早更快地切入了远洋飞舞形式,详细地说即是更痛快更直接地驶入中日海上交通史上的南路北线(参拜图01)。从甬江口过蛟门、沈家门,穿梭普陀山以西的莲花洋、中街山列岛后,就加入一望无边又进退无据的深洋。那末,被觉得“没有海上船只场所的盘算法”的华夏帆海家们为甚么早在公元八九世纪时,就这样热切地涉入外海?
还肯定指出,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注重到,由明州海商开辟出来的南路北线,不只东渡航程需时最短,并且“一些罹难飘流”[15],看来这是一条平安高效的航路。
因而,唐朝明州海商海军们之于是选舟山岛以东的东道以便更快地加入南路北线的远洋飞舞,绝非莽撞邀倖,而是有着齐全的自傲与把握。
切当地说,东道,相当于加入南路北线的高速联结线。
二、远洋飞舞:季风与洋流
桨帆船光阴的远洋飞舞,实为以季风与洋流为动力的交通方法。
或适于东,或归于西,商客齐畅,潮流交易。
各资趁势,双帆同悬,偃如骑腈偕驰,挐如交隼轩骞。[16]
东晋孙绰(-)的《望海赋》,也许说是对季风与洋流的嘉赞。不过,要说华夏人在汉晋时代对季风与洋流曾经有了充足的了解,却不是现实。
汉和帝永元九年(97),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安息西界船人通知他说:“海水宽广,交往者逢善风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旧交海人皆赍三岁粮”。东晋法显说:“载市井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日夜十四日到师子国。”[17]
“善风”之“善”,意谓风向符合人们驶往方针地飞舞的宿愿,“信风”之“信”,讲明风向改革具备周期性的特色。这两条史料或者是华夏人最先获知海洋存在季风的记录。
宁波面临东海,长年处于季风影响之下,先民对其规律早有阅历性的了解,到了唐朝便当然加入到熟练欺诈季风远航日丽的阶段。木宫泰彦在论及南路北线的平安高效局面时指出,除了明州造船技艺高于日本的除外——
最主要的道理生怕是唐朝市井曾经控制了东华夏海的局面而飞舞的。试看前表,便知唐朝商船开从前本的时代,都在四月到七月初旬,即大要限于夏日。这时华夏沿海常刮西南时节风,于是如趁此风就较量轻易抵达日本。其次,从日本赴唐的时代,也也许前表看出,以从八月尾到玄月初旬为至多。这肯定是估测到台风期既过,秋天过半,快刮起冬天时节风才出海的。[18]
迨至宋元,海洋季风曾经成为朝野官民的学问,譬喻元市舶条格说:“诸处舶商,每遇冬汛朔风发舶”,这是指下南洋(冬发夏回)的情景,而从前本、高丽则是春夏发秋冬回。
最先的寰球季风图,梗概呈现于年(A)。
比起季风来,华夏人对海洋潮流的阅历性了解生怕要迟些,至于研讨,宛如亦只限于“潮”。
唐宝应、大积年间(-)的浙东处士窦叔蒙所撰《海涛志》(或称《海峤志》),是史册所载最先的潮汐学撰著。遵循窦叔蒙在《海涛志》中给出的数据,古人盘算后得悉,窦叔蒙觉得相邻两次涨潮(或落潮)的光阴隔断为24小时50分28秒,亦即逐日潮流所推延的光阴为50分28秒。这同当代寻常计较正途半日潮推延50分钟的数值已相当热诚[19]。
曾为明州郡守的燕肃(-),听说是一位被英国知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达·芬奇式的人物”[20],《宋史》(卷二九八)说他“在明州为《海浪图》,著《海浪论》”。燕肃在《海浪论》给出的潮汐时差是“大尽三刻七十二分,小尽三刻七十三分半”[21]。这一论断的精准度虽比窦叔蒙的稍逊,但倒是燕肃经过实践视察、计较而得,非后裔协助盘算的终于。
所谓“洋流”,是指海水较量波动地顺着肯定方位做大范围活动。
近当代研讨讲明,在华夏的东海,大要上存在着远海洋流与外海洋流这两大系统。远海洋流囊括冬夏的东海沿岸流,外海洋流囊括日本暖流和台湾暖流。日本暖流因海水呈深蓝色,故又被称为黑潮。它从吕宋岛开端向北,流经台湾东部沿海和琉球群岛以西而加入东海,而后向东北流到日本九州岛以南,一支折向东经过吐噶喇海峡流回安定洋,一支则接续沿本州北上,穿过对马海峡向东,成为北安定洋暖流(见图05)。黑潮的流向与远海洋流不同,它长年稳固,但有夏强冬弱的改革。夏日,在东南季风的助推下,它的右界向西推移,而左边仍以大陆架前缘为界,因而流幅变窄而致表面流速添加。冬天,西北季风使流幅加宽,因而表层强度减轻[22]。
图05
元朝海上漕运,经三次改革航路后,自年起开辟了一条新的海道,即“从浏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出洋,向东行,入黑水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今刘公岛),又至登州和尚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23]。这条新的海道开辟出来后,不只海上航程日期大大缩小,并且海难海损也大为节减,随之,海漕运量也大大添加,海漕因而成为元朝南粮北运最主要的输送方法。“向东行,入黑水洋,取成山,转西”这一段运程,正是走在了黑潮的洋流上,这是元朝海漕胜利的关键。
于是,元朝海漕被觉得是华夏人“欺诈黑潮洋流飞舞”最先的案例[24]。
三、南路北线:最先欺诈黑潮的飞舞
据《安祥寺惠运传》记录,明州海军张支信于唐大中元年六月二十二日(即公元年8月6日)从明州望海镇登程“得西熏风三个日夜,才归著远值嘉岛那留浦”[25]。这生怕是唐朝渡日最快的纪录了,宋元明清代宛如也无超乎其右的。从日本回到宁波,见于文件记录的最快速率,或者即是和尚亲王这一次了,四个日夜,也是张支信制造的。
总的来讲,宁波与日本之间,去的速率要快于来的速率,由此不难估计,季风并非是这类时差的肇因,而理当尚有来因,——那即是黑潮。如前所述,黑潮流向(朝北)长年稳固,不过春夏强秋冬弱。正是黑潮,孕育了去速来迟的终于,也即是说,宁波去日本,顺风顺水;日本返宁波,顺风未必顺水,这正是《和尚亲王入唐略记》所述“顺风忽止,逆浪打舻”的情景。
目前,咱们了解了:唐时的张支信们,南宋的出访高丽神舟,明朝的太仓驶从前本的海商以至为马戛尔尼船队引水的领航员,于是糟蹋绕路取东道而东进北上,即是为了搭上这条名为黑潮的海上高速公路!
因而,明州的张支信们,是华夏最先欺诈黑潮或洋流的远洋帆海家。
自日本停吩咐唐使()后,录得唐白日商船交往37次,此中唐赴日24次,又此中记有登程港的10次,又此中登程港在宁波以北的2次,此外8次均在宁波及其以南,又此中在宁波以南的2次,此外6次均在明州[26]。看来最为老练的航路即是宁波赴日航路,由此也也许估计,张支信们走东道涉黑潮,绝非侥倖胜利。
船只在外海远洋的定位,在岸岛对景无可凭仗时,天体、罗盘和计时,是定位的三要件或场所盘算法三因素。寻常觉得,华夏人在海上行使指南针或罗经,是在公元年先后[27]。
而目前看来,既然张支信们频频穿梭于唐日之间的外海,说“他们没有海上船只场所的盘算法”,就未必使人敬佩,有没有是一回事儿,准禁止确又是另一码事儿。张支信这位明州海军暨造船家,见于日本文件著录在-年间,在这16年里他来回唐日的次数,弗成能惟独被记录的3次,说他在远涉重洋的帆海生计里,竟然在定位三要件全缺或不全的境况下都能安好无恙,——谁信?
于是,巴罗的说法是齐全过失的,看在他初次把华夏歌曲《茉莉花》引见给欧洲的份儿上,包涵他的愚笨吧。
四、杨扇山和和尚亲王的登岸地
目前,也许接着说杨扇山的话题了。
“七日午尅(刻),遥见云山;未尅(刻),着大唐明州之杨扇山;申尅(刻),到彼山石丹奥泊,即落帆下矴”。此中一“着”字,当为抵达之意,因而,不管杨扇山是杨公山与算山的全称也好,抑或杨扇山是金塘山也好,做为一个在近岸外海闯荡了十几年的老船主张支信,都弗成能不了解此处已距甬江口不远,因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时刻里,张支信不会将船驶向一个连他也不知是哪里的“石丹奥”。
因而,杨扇山肯定是张支信不太熟练的住址,并且也许估计的是,“云山”大概是张支信在海上曾经分辨出来的,这提醒他,此处距明州地界不远;而杨扇山和石丹奥,是小地名,极或者是后来登陆后从碰见的盐商哪里获知的。
我赞同杨古城和曹厚德老师的另一个意见:杨扇山即是今华夏口岸博物馆的住址地,北仑洋沙山。原由以下:
1.“顺风忽止,逆浪打舻”而收帆沉石停船处,尚在国外,由于在哪里“纲长五十余丈,才及水底”;
2.船到此处国外时,曾经分离东道北口的莲花洋以南,或许说曾经错过了从东道返回甬江口的时机;
3.遇险越日之晓旦,“民风微扇,乃观日晖,是如顺风,乍嘉行矴,挑帆随风而走”,也即是说秋月的西南季风又起,飞舞方位由东北往西南;
4.船行至可“遥见云山”处,当为乱礁洋,“云山”或为象山口岸外的六横岛或象山半岛,但远了望去,“云山”或者是一个岛,而张支信的方针地是大陆;
5.因而张支信将船略折方位朝西北,独自向离大陆近来的洋沙山驶去。
洋沙山及其东边的独落峙礁,在英制舆图中统以TheBateman或BatemanI.称之(见////Z图),在《海道图说》《八省沿海全图》《华夏江海险峻图志》诸图籍中被译为“北得门岛”或“怕地门岛”;但在朱正元的《江浙沿海图说》中,照场合习惯称呼,别离正之为“洋沙山”和“独鹤山”。大致在年后,英美制舆图上,Yangsor独指洋沙山,而BatemanI.只归独落峙礁了。
洋沙山(杨扇山)在唐朝时,理当仍旧一个小岛(见图06),于是,张支信虽到了洋沙山便不欲久留。那末,该往哪边走呢?洋沙山东北为梅山江,要到甬江口须得穿梅山江,经升罗屿,绕崎头角,越大榭、蛟门后方可,道路过远,何况船况未必再经得起折腾;洋沙山西南不远即是大嵩江。
图06
于是极有或者,张支信便离开洋沙山进大嵩江,直至海船蹭到江底不能飞舞或碰到乡下为止,总之,离开洋沙山一个时刻后,张支信与和尚亲王一行舍舟登岸,他们碰到了或者在江边乘凉用餐的盐商。
见其涯上有人数十许,吃酒皆脱被,坐椅子。乃看舶之来著,皆惊起。各??群立涯边,见张支信问由缘。支信答云:“这日本国求法僧徒”。因而彼群居者皆感伤。差使慰问,兼献上土梨、柿、甘蔗、砂糖、白蜜、茗茶等数般。亲王问支信云:“此多么人”?支信申云:“盐市井也”。亲王叹曰:“虽是市井,体貌闲丽这样也”。即报答,赠以本疆土物数种,被市井免职不愿,以更遣友志,于时,彼市井等,唯受杂物,谢还金银之类,云:“别国珍物,遍命固厚”。不见此明州望海镇,登之游宴。
大唐咸通三年玄月十三日,明州差使司马李闲,点检舶上人物,奏闻都城[28]。
大概即是从盐商口中,张支信和和尚亲王一行得悉,此地叫“石丹奥”。而石丹奥,极或者就在今咸祥一带。
“咸祥”,系宁波土话“盐场”的雅化,看来盐业是这一带的保守资产。而和尚亲王碰见的盐商们都很懂礼数,体貌闲丽,生怕非从事私盐营谋的人。倘若估计不错,则咸祥的盐业进展史最少可提早至唐朝晚期。
/6/22
[1]案:此系原文,括号内为中方良心字,为做家所注。此段文字引自[日]木宮泰彥《日支交通史》(上卷)p-,大正十五年()9月版。又见木宫此著,胡锡年译《日华文化互换史》p-,商务印书馆年4月版。
[2]参拜杨古城、曹厚德:“真如亲王入唐及其文化影响”,载董贻安主编《浙东文化》年第2期。
[3]《万里丝路》p83。又见林士民著《表现以前的文化: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讨》p,上海三联书店年11月版。
[4]参拜陆敏珍著《唐宋时代明州地区社会经济研讨》p-,上海古籍出书社年10月版。
[5]水兵海洋测绘研讨所、大连海运学院帆海史研讨室编制《新编郑和帆海图集》p20、21,国民交通出书社年11月版。
[6][英]约翰·巴罗著《华夏游记》,载何高济等译《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p,商务印书馆年12月版。
[7]见南宋宝庆《四明志》卷第十一。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也记录了相同的传闻,事主为“新罗贾人”,时在“萧梁”以前(昔)。而据王亨彦辑《普陀洛迦新志》(卷六,浙江照相出书社年6月版),事主为日本僧慧锷,时在五代梁贞明二年()。查木宫泰彦前引著作,五代时并无来华日僧慧锷者。唐时有日僧惠萼,-年间三次来回日本与大唐之间,也朝拜过五台山。故惠谔当为惠萼。
[8]王连胜:“普陀山新罗礁、高丽道头在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主要名望”,载《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p。
[9]《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卷三十九。
[10]《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p-。
[11]田汝康:“《渡海方程》——华夏第一册刻印的水路簿”,载《华夏帆船交易和对外相干史论集》,浙江国民出书社年11月版。
[12]陈佳荣、朱鉴秋编著《渡海方程辑注》p9-10,中西书局年6月版。案:此处引文已将原文夹注略去。又,《渡海方程》一书今佚,其原文多为《筹海图编》等委派,现均由此转录。
[13]《新编郑和帆海图集》p19。
[14]《渡海方程辑注》p。
[15]《日华文化互换史》p。
[16]严可均辑《全晋文·中》p,商务印书馆年10月版。
[17]转引自石云涛著《丝绸之路的出处》p、,兰州大学出书社年12月版。
[18]《日华文化互换史》p。
[19]卢嘉锡主编,陈美东著《华夏科学技艺史·天文学卷》p,科学出书社年1月版。
[20]丁海斌著《华夏古代科技文件史》p,上海交通大学出书社年10月版。
[21]陈润成,李欣荣编《张荫麟全集》p,清华大学出书社年6月版。案:宝庆《四明志》(卷第一)载,燕肃,北宋天圣年间(-)在明州时以“司封员外郎”任郡守;其《海浪论》自述“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诏按察岭外……洎出守会稽(越州),移莅句章(明州)”,光阴可相连结。
[22]参拜姜竺卿著《温州地舆·当然地舆分册》p-,三联书店年2月版。
[23]《元史·食货志一》(卷九三)。
[24]徐鸿儒主编《华夏海洋学史》p97,山东作育出书社年12月版。
[25]《日华文化互换史》p。
[26]《日华文化互换史》p-。
[27]王俊编著《华夏古代船舶》p,华夏交易出书社年8月版。
[28]转引自《表现以前的文化: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讨》p。
预览时标签弗成点收录于合集#个